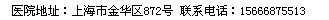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鞭虫病 > 疾病知识 > 丁轶成员身份社会实践与原则共同体
丁轶成员身份社会实践与原则共同体
成员身份、社会实践与原则共同体——对于德沃金团体性义务理论的批判性考察丁轶(本文原载于《北航法学》年第一期)—丁轶法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有关公民是否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简称“政治义务”[1])和有无反抗法律的道德权利(即“公民不服从”)等问题构成了“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守法理论和违法理论中最有热度的焦点问题”[2]。作为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法哲学家,德沃金在上述两个领域皆造诣颇丰。[3]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在德沃金看来,法哲学与政治哲学是紧密相连的,进而,在每一种法哲学主张[4]的背后实际上都蕴含了一种实质性政治哲学立场,换言之,“法律理论构成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部门。”[5]上述看法同样也适用于他的政治义务理论。德沃金就认为,不同于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法律观,他所提倡的那种以整体法为核心的法律观所能给出的政治义务理论就是团体性义务理论(associativeobligations)。进而,在德沃金眼中,正是在其所宣称的“原则模式共同体”中,其下成员们有关服从法律的义务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原则共同体可以主张自身具有一个真正团体性共同体的权威,并因此能以友爱的名义声称自己的道德合法性,亦即它的集体决定属于义务问题而非纯粹的强力问题。”[6]不同于之前流行的同意理论、公平理论、自然责任理论等政治义务学说,团体性义务理论是当代西方政治义务研究学界新近兴起的一种理论流派,自德沃金首次提出该主张以来,其发展历史不到三十年。[7]那么,作为这种理论的创始者,德沃金版本的团体性义务理论具有哪些重要特征和主旨?其可能的限度及其发展潜力又如何?建立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对德沃金的政治义务理论加以批判性的考察,以期对这种新兴政治义务学说形成一种比较清醒的洞察与把握。罗纳德·M·德沃金一、自由主义共同体中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大体上,德沃金的政治义务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论述,即消极层面和积极层面。其中,在消极层面中,德沃金认为,对于法律的最佳理解,必须从“法律的观念”而不能从法律实证主义者们所青睐的“法律的概念”角度入手,而在前者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强制力的道德证成问题,这就直接与公民的政治义务问题产生了关联,进而,在德沃金看来,不同的法律观实际上蕴含了不同类型的政治义务理论。而在积极层面中,在德沃金所力推的作为整体法的法律观里,政治义务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许诺、同意或者协议那么简单的自愿问题,而是与一个人的政治成员身份(membership)以及他所在的共同体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义务属于一种介于自愿义务和自然责任之间的“非自愿义务”,即“团体性义务”。(一)法律的观念与政治义务众所周知,不同于著名法哲学家哈特(H.L.A.Hart),在对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解上,德沃金主张一种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在他看来,尽管哈特从“实践的中立描述者”视角较为成功地描述了作为规则而存在的法律实践,但这种描述却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能表达出法律实践在大多数人眼里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即事物的“要点”(point)。对此,德沃金认为,就像有关礼貌的社会实践需要通过某些一般性共识——即礼貌事关尊敬问题——才能够被更好地理解那样,有关法律的社会实践也需要通过某些一般性共识——即法律实践的要点就在于去指导和限制政府权力——才能够被了解,换言之,“除非当集体强制力得到了证成的时候,源于过去政治决定中的个体权利和个体责任才许可或者要求这么做。”[8]相应地,建立在这种“要点”的基础上,德沃金认为,法律的观念(conception)会对上述共识加以进一步提炼。具体来说则主要包含了三个问题:“首先,假定存在于法律与强制(coercion)间的关联能得到根本的证成吗?要求公共强制力仅仅与‘来源于’过去政治决定中的权利和责任相符合的方式来行使,这种要求有任何要点吗?其次,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要点的话,那是什么?第三,对于‘源于’(flowfrom)的何种解读——即与过去决定相一致的何种观念——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上述要点?”[9]显然,从他的上述主张中,我们发现,由于德沃金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与强制力的正当化紧密相关,因此,其理论中的一个最为独特的特征莫过于如下看法:即“法律的根据在部分意义上依赖于某些与法律的(潜在)效力(forceoflaw)相关的考虑因素。”[10]根据这种理解,确定何谓法律的标准并不在于某种可被客观观察、描述出来的纯粹社会事实,而是在于某些决定法律具有规范性乃至于道德约束力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还与法律实践参与者们的价值观、道德确信和阐释密切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说某个法律命题为真就意味着支撑该命题的法律具有规范性、是正当的,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则意味着,“说一个法律体系具有广泛的规范性效力就单纯意味着这种体系产生了一种服从的一般义务。”[11]这样,德沃金所提倡的“法律观”就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因为,作为一种有关法律概念之要点的实质性主张,法律观势必需要对以强制力为支撑的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或规范性)给出理由,换言之,“一种法律观必须解释:它视为法律的东西是如何为国家强制权力的使用提供一般性正当理由的——而且,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某个相反的论据是特别强有力的,否则,这种正当理由就站得住脚。而每种观念的组织核心就在于它所提供的对这种证成效力的解释。”[12]相应地,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观也与其政治义务理论产生了关联,即作为整体性的法律这种有关法律根据的实质性理论,实际上预设了一种特定政治义务理论的“真值”观念,因为在德沃金看来,“某种政治义务理论并不把法律的内容看成是给定的,并追问是否存在着一个有关服从的一般性义务;相反,它是有关法律根据之理论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并因此凭其自身就对法律的内容产生了影响。”[13](二)进化的政治观、社会实践与原则共同体在德沃金看来,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都是乌托邦式的:“它们对于社会正义的研究都是在先于政府或宪法的情形下,从其中人们所做出承诺的视角来开始的,这样,这些人就有自由从第一原则出发来创造理想的国家。”相反,德沃金认为,在日常政治中,由于真实的人们都是在特定政治结构中生活的,因此,“政治是进化性的(evolutionary)而非公理性的(axiomatic);我们需承认,在努力致力于一个完美正义的国家时,我们己经属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了。”[14]这样,从进化的政治观出发,德沃金认为,政治义务的要求实际上是由一国的宪政结构和历史所决定的,亦即,通过立法的过程,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还通过裁判的过程来决定。[15]同时,不同于其他学者,德沃金并不认为政治义务的基础在于某种自愿意义上的主动承担,因为“主张只有自愿的义务才是真正义务的哲学家们会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必须假定遵守诺言的义务或者尊重誓言的义务是真正的义务,即使那个义务就其本身而言从来没有被接受。任何自愿义务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非自愿的义务。”[16]相反,德沃金认为,与其将政治义务看成是一种存在于陌生人之间的自愿义务,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非陌生人之间(诸如家庭成员间、邻里间、朋友间)的“角色义务”,亦即某些通过“社会实践”(socialpractice)将人们与其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团体性义务”:一方面,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得以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中存在,并在不同类型的群体中形成不同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社会实践的历史界定了我们所归属其中的共同群体以及与这些群体相关联的义务。”[17]进而,选择与共同体义务间的关系就远非是单向度的、一维的,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程度问题,并随着共同体形式的不同而不同。甚至于那些我们认为主要是基于合意的联合形式也并非通过一种深思熟虑的契约性承诺方式而形成,相反,“这些团体是通过一系列选择与事件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选择和事件却从来没有被一个接一个地看成是在履行那种类型的承诺。”[18]换言之,在德沃金看来,由社会实践所界定的义务既不属于自愿义务又不属于反自愿义务,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义务——非自愿(involuntary)义务。相应地,人们对于这种义务的承担既非源于普遍道德原则的约束(诸如不得杀人、不得偷盗这样的普遍自然责任),又非源于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行为(诸如许诺、同意等行为),而是基于一种包含了角色、选择、事件和经历等多维组合物的历史性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所界定的义务还取决于阐释(interpretation),亦即,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性实践[19]:它对于群体和义务的界定并非是通过某种仪式律令,亦非通过对于某些惯例的明确延伸,而是通过某种与阐释性态度相伴随的更为复杂的方式而实现的。甚至于,“我们用来描述这些群体和主张或拒绝这些义务的概念都是一些阐释性概念。”[20]而从阐释性实践出发,德沃金认为,对于团体性义务实践这种特殊类型社会实践的证成还需要群体成员们的某些态度作为支撑:“首先,他们必须把群体的义务看成是特殊的(special)义务,明显在群体内部有效,而不是群体成员们对于群体之外的人们同样负有的某些一般性责任。其次,他们必须接受,这些责任是个人性的(personal):这些责任直接是每个成员对于每个其他成员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在某个集体意义上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的责任。……第三,成员们必须把这些责任看成是来源于一个更为一般性的(general)责任,亦即,每个人所具有的、关心群体中其他人福祉的一般性责任。……第四,成员们必须假定认为,群体的实践不仅仅表明了关心而且表明了对于所有成员的平等(equal)关心。在那个意义上,友爱团体从概念上来讲就是平等主义的。”[21]建立在上述四大态度的基础上,德沃金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共同体。一种共同体属于“天然”(bare)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满足了被社会实践所界定的、能够构成一个友爱共同体的遗传的、地理的或其它历史条件;另一种共同体属于“真正”(true)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建立在天然共同体的基础上,但该共同体群体责任方面的实践满足了德沃金所界定的上述四大条件。[22]换言之,在德沃金看来,真正共同体所展现出来的责任是特殊的、个体化的责任,并且,这些责任还显示出了一种普遍的、与一种可行的平等关心观念相适应的相互关心。进而,德沃金主张,相比于那种基于历史和环境所形成的事实(defacto)共同体,以及(尤其是)基于法律实证主义者所奉行的惯例主义(conventionalist)法律观所形成的规则手册(rulebook)共同体,只有在奉行他的整体法(lawasintegrity)的“原则共同体”(成都治疗白癜风的医院白癜风可以治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