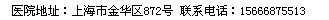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鞭虫病 > 相关医院 > 丁老师心中抹不去的一道疤难忘和妹妹一起
丁老师心中抹不去的一道疤难忘和妹妹一起
抹不去的记忆
——难忘和妹妹一起度过的日子
我比妹妹大两岁,妹妹也快五十岁了。
记得小时候妹妹经常无端地被我欺负,原因除了我坏我年龄比她大,还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本见不入她在父母亲的怀里卖乖撒娇。妹妹既听说又像话,经常如跟屁虫一样偎在爸妈的膝前打转转,她很会讨父母亲的喜欢。记忆中父母亲从未动过她一指头。我反而由于懒惰或坏点子多,往往招来父母不少打骂。所以每当我和妹妹独处的时节,我就会见缝儿报复她,只凭我的力量比她大。
我和妹妹去毛鬼沟抬水,母亲安付说妹妹的力气小,要我给让担儿。而我偏不听,却把挂下井的绳钩儿放在担儿中间,这样一来,走下坡路时大部分分量就落在妹妹肩上。她个子小,走前面,走不稳当,双手扳住担头子左右打摆摆。她说重地很,缓一下,我说再走十步吧。只有快到家的那一肩,才把绳钩儿移到离我较近的地方,目的是要让母亲看见我确实给妹妹让担儿了。
我和妹妹去邻居家磨堂里推磨,两个磨提拴两个绳环,两根绳环套两根磨棍,两根磨棍横在我和妹妹胸前,我俩使出相同的力,磨盘才会均匀地转圈圈。脚下扬起的土雾,加上循环往复无聊的旋转,一阵阵就使人头晕目眩。我便动歪脑筋和妹妹商量:把没推完的麦子往磨堂旁的麦衣里埋一部分,这样既省时又省力,早些推完早耍子。但妹妹不同意,她说妈妈发现肯定会打死的。阴谋未果,产生情绪,推着推着我忽然猛地用劲推一把磨棍,妹妹被闪空,丢了磨棍,展展地趴在地上,我趁机挖了两把麦子抛向麦衣……
后来,不让担儿和抛洒麦子的事情都被妹妹告了状,当时我被父亲扳倒在地,屁眼上一顿巴掌,打得我心上都热辣辣地疼;母亲去找寻推耙儿或烧火棍,她还未找到时,我已经拔腿而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妹妹的怨恨也是与日俱增。
饥饿的折磨,瞒不住眼睛瞒不了心,更瞒不过被食欲不断撕扯着的胃。趁家里没人,我翻墙越壁进去找到家里唯一的半笸箩扁豆,胡乱掬几把急忙忙倒在锅里炒到发焦,兜里装一部分先吃,其余设法隐藏。当我躲在柴垛子背后独享其乐时又被妹妹发现,她哭着要着不行,我便分给她一饿把,以堵住她的馋嘴。
一次我偷着去热半碗残饭,没经验,又焦了。关键时刻,妹妹总会出现。她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然后可怜兮兮地说:“大哥哥,咱两个吃,能成不?……”那次我把烧焦的都给了她,妈妈说吃上焦疤儿拾钱呢。
妹妹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却给她一条羊鞭,母亲给了她一只背篼。忘不了那一瞬间,妹妹的神情呆了,眼圈红了,她说“我要念书呢!”紧接着眼眶里的泪水就刷拉拉掉了下来,像两串断了线的珠子,悬在妹妹胸前。妈妈把妹妹揽在怀里,说:“心疼的,嫑哭,念书不好,老师打呢,放羊能挣工分么,还不挨打,我的娃,听话……”父亲脸上挂着个苦笑,干脆躲进屋里。
家里就只有我一个念书的人了。
放羊归来,妹妹会坐在我的对面,看我写字,好奇地打开我的课本,把眼光停留在书中的插图上,辨不来就问我,我装模作样地给她讲,辨来了一点,她就笑。
早晚放两趟羊,妹妹弯着腰背回来两背篼草,喂猪的,晒柴的,由母亲分类,妹妹则急匆匆去厨房,咕咚咕咚一次性喝下半马勺凉水,用手背擦着汗,抹着嘴,打着饱嗝,爬在炕上倒头就睡。妈妈的饭熟了,她还没有醒来。
我没搞明白,妹妹那时哪来那么多的瞌睡?
临近年关,那时我十岁刚过。生产队放假半月,妹妹也休假不去放羊了,父亲留在家里照看年幼的弟弟,母亲、我和妹妹三人去川区讨饭。三十多里山路,母亲一路讲着她去宝鸡、西宁、海石湾、中卫等地要饭的见闻感受,间接给我和妹妹传授要饭技术,强调注意事项以及相互间的联络方法……
从苟家庄开始,我和妹妹尾随着妈妈,一直讨要到雒家庄。我那两根腿就像缀了石头一样,挪不动了;脚底板也疼得如针扎一般,已经连丝都拉不动了。第一次见到嘶吼彪驰的火车,我就开始耍赖皮,坐在火车道旁,寸步不移了。母亲拿我没办法,就把我安排到距离火车道不远的一棵大树下,等于满足了我的要求,又便于母亲寻找,如此这般千叮咛万嘱咐一番,妈妈便领了妹妹继续去讨饭。
傍晚时分,高音喇叭里传来找人的声音。原来我早已把母亲的安付统统抛在脑后,等不及下一趟火车到来,我独自进村,看人家川区娃娃穿的炫衣裳、吃的白面馍馍、玩的我没见过的游戏,还去认人家墙上写的“万岁”标语……一位老大爷问明白我的情况后,领我到饲养院,我终于得以和母亲、妹妹团聚。母亲眼含泪,脸上笑,妹妹只看着我傻傻地乐,还说:“大哥哥,你跑到哪里去了,把妈妈都急哭了。”我那么小,哪里知道妈妈的心思啊?
睡觉的地方就在饲养院的草房子里。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饲养员抱进来一床半旧破棉被,还端来一碗开水。妈妈和妹妹讨吃了晚饭,而我错过吃晚饭的机会。就着开水,我吃了母亲和妹妹讨来的白面馍馍——那是童年的我尝过的最美味的食品了!钻进被窝,妹妹很快就拉起了鼾睡。唉,我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土鱼儿、扎撒、麻鞋底浑身乱跑,我不停地抓挠,虫虫儿就乱咬,天亮起来,三个人脸上都是包。但是妹妹睡得太沉,她竟然不知道……
经过三天的见习,第四天在头甲庄开始了我们的分组讨要。我和妹妹一组,母亲一个人一组。一个巷道,我们分别从两头向中间夹击。
我自幼儿脸皮薄,还死要面子。每当进了人家的门,便羞于开口,心里直打鼓。每次总是把妹妹推搡到前面,正对着人家房门,艰难地喊出那一声“阿姨——给上点……”过不到十秒,再重复一遍,直到有人出来。有的人就拿我和妹妹调侃:哪来的这么小两个娃娃,姊妹两个吗,你爸你妈呢?——这属于好的;更有甚者问:你俩是干什么的?妹妹答“要面的”,他就会问:馍馍要不要,洋芋要不要,饭要不要,水要不要……都是些母亲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和妹妹无力应变,被问得面红耳赤,搓脚挼手,到处找老鼠窟窿。于是只好羞愧地扭转身哭着离开,身后便及时传来一串奸邪的嘲笑。
一家门里有一次挨个儿进去三个讨饭的,掌柜的心烦,眉毛拧成了绳,前后打量一番,只丟给我和妹妹一个刀把儿馒头,另外两个直接一句“往出去滚”就打发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娘仨不是没遇上过……
到了吃饭时分,必须将藏于背篼底的洋瓷缸子端在手心,碰上吃饭的人家渴望人家施舍一勺子汤饭过来,虽然是汤多饭少,但妹妹每次都是让我首先吃饱,她看着我咀嚼、咽下,自己则随着我的动作往下咽口水。
离开了母亲的保护,川里娃还想办法惩罚我和妹妹。脊背后的背篼里察不着就被放进石头,越走越沉;最怕他们烧狗,本来狗爱咬穿烂的要面客,再加上他们的暗中怂恿,冷不防那狗便从身后悄无声息地袭来,妹妹吓得失魂落魄,哭喊着“妈妈”抱住了我的腰,我放出瓜胆抡起讨饭棍招架烈狗,那狗会咬住棍头不放。那群恶作剧的少年见此开怀大笑,就像观看耍猴表演。从那次得到的教训是,妹妹必须在前,棍不离手;我来断后,手不离笼畔,时刻警觉狗的进攻。
一个礼拜的讨要取得了丰硕成果,妈妈一背篼各色干馍,我和妹妹各半洋面袋子面粉,背在肩上,三缓四歇,好似凯旋的将军,怀揣无比喜悦之情,经由卢家山上山回家。半山腰,我们和前来接应的父亲会合。一家人可以美美地去过年了……
最后一次是五年级时的腊月二十八,我和妹妹结伴去讨饭——妈妈没去成。从包家山到年家湾、塔山、海池,再到张家沟、李家沟。我依旧放不下身段,拿不下脸,最大的困难是顿数上要不上饭。妹妹倒反比我开创地多,她面善嘴甜,脚底板还跑得连欢。妹妹总是把先讨来的饭腾腾腾端来给我,我先吃着,她再忙不迭地挨门挨户去要。
借宿在张家沟饲养院高房上的那个夜晚,老天变脸,大雪封山,行路难。我和妹妹本来打算在张家沟讨要半日后,赶在接先人之前到家。没想到张家沟的娃娃比川区的还啰然,他们十几个人拧成一股绳,在“绳头”的指挥下,手拿石头砖瓦,把我和妹妹当作活靶子练投弹。妹妹一路打掩护,我俩忙不择路,落荒而逃,不设意钻进一条水沟。消融的雪水湿透了我和妹妹的烂布鞋。所幸摆脱了神枪手们的追赶,清理出背篼里的砖石瓦片,归心似箭。一路跌跌撞撞,昏踞踉砍,来到西庄梁时天已擦黑,四只脚被冻得没了知觉。父亲业已在梁上等候了,稀稀洒洒的炮仗声“啪啪啪啪”地从夜空划过。
到家后,父母听了妹妹的哭诉,一家人就被泡在泪水里。热腾腾的土炕上,母亲拥着妹妹,父亲握着我冰凉的双脚,弟弟不知所措地缩在炕脚发呆……
由于生活所逼,妹妹不到十五岁就定了亲事。父亲用她的彩礼钱开销欠账,打点日月,供我读书。我读完了师范,妹妹放了近十年羊。我工作了,妹妹出嫁了。她认不得字,看不懂电视,玩不转手机,自嘲是个睁眼的瞎子。每当回一次娘家,偶尔抱怨父亲没让他念书的事,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欣慰的是,妹夫既勤快又知冷暖,她们的三个孩子也有两个考上大学。
然而妹妹,大哥哥此生欠你太多,叫我怎么偿还!
作者简介丁兴芳,男,50岁。甘谷县谢家湾乡西庄村人,甘谷在线驻谢家湾通讯员。年毕业于原天水地区渭南师范学校,后通过自学获得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及本科学历。现在甘谷县谢家湾乡丁家沟九年制学校任教。中科白殿疯医院怎样才能治好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