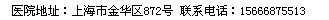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鞭虫病 > 预防治疗 > 04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04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通常人们认为,一切发生在我们自身身上的意外都是始料未及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意外了。但有一个人,他曾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却平静的思索着绝对的时空观,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创作,独自一人发明了广义相对论——上帝是不会只骰子的——他说。
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宠物——一只长脸獠牙、鼻梁鲜红、蓄着山羊胡子的赤道几内亚大马猴——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小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不过他是、但不仅仅是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小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他拥有地球上所有的名字或什么都不叫,他是每一只赤道几内亚大马猴以及马猴的整体以及根本不是马猴。
他的存在很难解释。他出于一个看似的意外掉落在达尔文“小猎犬号”的甲板上,几乎同时的掉落在爱因斯坦位于苏黎世和柏林的笔记本上,这就促使上述两人耗尽一生企图寻找和揭示大马猴存在的真相。曾经几度,他们离真相已经非常接近,但最终还是误入歧途。
而大马猴,差不多在显生宙时期,就超越了自己认知的极限,占据了整个地球的里里外外,从空气中摩肩擦踵的粗糙的颗粒,到地幔里头汩汩冒泡的热汤,无所不在。作为东毗提诃兽变异的后代,大马猴在短短几百万年中,吃光了几乎全部的恐龙。
威猛先生在其《威猛先生的资深假装逼不得已旅行指南》里曾经采访过这样一只马猴。透过赤道几内亚英属皇家动物园的笼门,这种头戴脸谱的暴戾动物一阵手舞足蹈的吱吱啊啊的吼叫过后,从屁股底下翻出了一片银杏树秋后金黄的叶子,特写奇怪的停留在叶片上被虫啃过的细小洞孔。这一组深受电视台诟病的镜头组接在首发上映之后便被剪掉,往后任何版本中都没再出现。
很有可能,威猛先生是继爱因斯坦和达尔文之后地球上又一个发现大马猴秘密的人,他曾在自己被销毁的手稿中指出:这是一个极不科学的现象,因为正常情况下一只怀孕的东毗提诃兽会选择低光度、高密度、高温度的白矮星作为产卵的最佳地点。地球,对新生的东毗提诃兽而言,环境太过贫瘠,根本无法生存。如果真要想理解大马猴,就要先理解狗,理解长颈鹿,理解花、鸟、爬、虫,理解海洋深处由各种鱼类组成的骨刺和鳞片,理解这一切现象的祖先东毗提诃兽、南阎浮提兽、西牛贺兽、和北俱芦兽。
大约一百亿年前,很多老人都还记得发生在那时候的宇宙大饥荒。几乎所有的能源性食物都耗尽了,古宇宙的寿命走到了末期,大多物种遭受生存的威胁或者濒危。宇宙食物链的王者、残忍的侵略型游牧种族东毗提诃兽,也不得不效仿弱小动物那样成群结队的,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张,在宇宙各处繁衍,疯狂的使自身陷入“失去共栖物”的时代。
而宇宙,也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还击。它开始暴涨,使万物分离,无论多么强壮的东毗提诃兽都无法跨越,一夜之间产生的距离足以把异性隔绝在遥不可及的世界。
原来拥挤、明亮、霓虹色的宇宙改变了。
为了寻找新的适宜生存的环境,百分之八九十的生物在漫长而黑暗的迁徙途中死亡。它们的尸体,在宇宙中漂泊、聚合、塌缩、又分离,形成了奇怪的以前没有的物质。
最终,宇宙自身也发生了分裂。它沿着维度的曲线,一分为四,裂变为碟形、扇形、梨形、矩形四个空间。里面分别关着东毗提诃兽、南阎浮提兽、西牛贺兽和北俱芦兽,他们失去了同伴,独自漂流,靠自我复制繁衍后代,被视为宇宙中最孤独的生物。
一些赶在分裂前逃脱出来的东毗提诃兽,受到能量风暴压的驱赶,经过漫长的迁徙,不约而同的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地球。这是一颗非常非常新鲜柔软的婴儿星球,它需要的能量少得可怜,仅依靠恒星散发出来的光和热就能维持生命。
所有从宇宙大饥荒中逃逸出来的生物在到达这里时都发生了异化,它们穿越大气层,被分解成很小很轻的微粒,在空气中飘荡,缓慢降落。历史上的古宇宙不复存在了,但是新的更丰富的生命得到了机会,以各自心目中最理想的形态重新生长出来。
一只叫做领鞭虫的单细胞生物经过自身独特的思考,和一系列革命性的沟通、联系其他蛋白质,不懈的促进着单一生命体之间的聚合,终于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么一个基因变异,为如今的全人类定下了基调。
六亿年后,一艘代表着地球最高文明的飞船,为了寻找生命大爆发的真相,“意外”的导致自己母星和上面的一切毁于一旦。可是据其他星球回忆,这颗忧郁的小蓝星曾给这个世界留下过一条最后的信息,人类可以解读为: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很多来自古宇宙的生物,他们因为保留着四个以上维度的生命特征,拥有跨越时空的感知力,他们想尽方法向人类做出预言,比如大马猴掉落在达尔文“小猎犬号”的甲板上、几乎同时的掉落在爱因斯坦位于苏黎世和柏林的笔记本上。可是人类这种诞生在狭隘维度的新宇宙生物一直没能成功解读,于是“意外”就发生了。
一些对人类并不那么友好的生物,则从一千五百年前开始陆续离开,集体迁徙的盛况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为了加入这场运动,人类(据不完全统计有那么百十来个吧)在一九九一年首次提出“自愿灭绝”计划,并用上百年时间逐渐衍变成了一个相当小众的音乐厂牌。十三岁的少年蝉曾在一场重金属音乐节上成为自愿灭绝乐队的粉丝,买了他们的签名专辑,还在支持者名单上签了字。
这件事被蝉在第二天的戒断反应中忘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二十年后巴比从床底下把那张专辑拱了出来,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想起这段经历。
“Isu,那是她的名字,”关于初恋,蝉回忆道,“真是一段屈辱史。我花了一整个学期企图靠近她,结果她用一大瓶掺了迷幻剂的烈酒没过半夜就把我撂倒了,那些对她献殷勤的男生在我躺倒的身体上踩来踩去。之后三年我都没敢再跟她说话,直到她考进天才学园,我彻底失去了她的一切消息。往正面了说,Isu教我总结出人生总是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
“我想,你说的这个人现在离我们不远。”白龙说,并掉转了船头,正面舷窗里远远的出现了一个蹦蹦跳跳的光点,接着是一架闪闪发亮的小型飞行器。
这架飞行器像一只水熊虫般姿态缓步的向他们驶来,速度却意料之外的惊人的快,那一闪一闪的荧光质的小头壳后面连接着巨大无比的炭黑色船身,船身外裹着一层厚厚的胶质的水膜。两船相错,黑虫在白龙上方展开了望不到边的鞘翅,嶙峋的腹板鳞次栉比的暴露在蝉的舷窗前。
白龙逆着黑虫的肚子滑行了很久,景色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此近距离却只能窥见对方一斑的体型差通常可以震慑敌人,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但却让蝉感觉就像从火车茅坑里观望一截无限循环的铁轨。
“这是Isu的飞船?”
“不,这是巴克山族的飞船。”
蝉听了白龙的回答,怔怔看到黑虫最后甩出一条尾节藏有病毒毒腺的尾巴,以惊人的速度缓步消失在目光顶头。
“你是说Isu在巴什么族的飞船上?巴什么族?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巴克山族。我知道你还有一大串问题要去问Isu本人,但是她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要我说,你全部都理解成人生总有些追悔莫及的意思就可以了。”
蝉的心里产生了一些微妙的震颤,他很难解释这种体验,也无法传达。自从二十一世纪人类推翻了持续了一百年的人文主义,开始推崇智能,就失去了对体验的热情。曾经人们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和金钱去旅行,乐于沐浴爱河,喜欢消费新鲜和刺激的事物,而现在这些都变得无关痛痒。现在,人们需要的只是不断提升AI的性能,帮助自己聊天时可以快速的检索信息,做爱时可以精准的找到G点,心神不宁时也不再需要安慰而是一剂吗啡。
可想而知此时的震颤对蝉而言是如此陌生,涟漪一圈一圈扩大无法停息,以至于蝉的手指都开始颤抖。
“人类可以跨越时间的维度感受如此深刻的大羞辱,却对机器人的悲痛全然不理,好像他们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情绪化一样。”罗汉焦躁不安的在飞船的各个舱室间溜达,这会儿刚好走到蝉旁边。巴比被大浴巾裹成一个襁褓,露出一个左顾右盼的湿答答的脑袋,在罗汉怀里“支——娃——支——娃——”的尖叫。
他们的前方,一张巨大的生物钢丝网已经悄然张开,一些水珠状的黏液一排一排的挂在横丝上面,像晾衣绳上的风铃等待着一触即发的碰撞。出于成本的考虑,缠绕在网目上的隐带也在等待,黏液的机关受到触发,这些隐带才会扑向猎物,沿着宇宙的空间曲率向周围展开、合拢,直到完全闭合,迅速收紧,把猎物裹缚其中。
蝉的飞船刚好撞在这张网上。或者说,是这张网早早就等在那里了,它通过对飞船的雷达进行干扰,引诱飞船驶进它的靶心。
“警告!”那张网说,“正在进行面部扫描识别。请把脸靠近舷窗。”
“什么?”仅仅出于生物本能的好奇,蝉一边质疑,一边已经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舷窗跟前。就连罗汉和巴比也跟了过去。
接着一团黑乎乎的飞虫蜂拥而至,瞬间从外面爬满了窗户,他们瞪着几千万对造型突出的复眼,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这他妈是什么!”蝉大叫,跳着脚,快速的向后跃起,“我最他妈讨厌虫子!”
“巴克山族。”白龙说,“他们是定居在地球上的节肢动物门外星生物,但实际上这么说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全部加起来才是一个整体,拥有共同的意识,这些意识存储在缓步动物门体内。”
“但比起大马猴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罗汉说。
巴比在罗汉怀里不屑的“哼”了一声。
虫子们停止了交流,统一望向一个方向,貌似是等到了一声令下,呼啦一下飞散开。
“你们被捕了。”巴克山族这时发出通牒,“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陪审团成员目测你们就是星际通缉要犯。现在立刻打开舱门,让我们的执法人员登船,以便对你们进行公正的裁决。”
“来吧,我正想讲讲大马猴呢。”罗汉说。
“不。我们应该立刻逃跑。”蝉说,“以人类经验,永远不要相信什么公正的裁决。”
飞船开始向后倒退,拉动横丝上的黏液。黏液越抻越长,将飞船死死拖住。隐带则从另一个方向飞扑出来,它先吐出一根细长的舌头,冲到飞船跟前,怦然张开,用四分五裂的触手扣住飞船。它闭合,再收紧,将飞船紧紧裹缚。
“嗯哼,这下好了,他们不会听我讲大马猴了。没有人关心我想讲什么。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没有人听我说话。完全没有。”罗汉沮丧的垂下双手,抖落浴巾。
巴比扑通掉了下来,就地一滚,跑了。
“罗汉。”蝉叫他。
罗汉打断了蝉:“罗汉罗汉。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把缠在飞船外面的那些恶心吧啦的蜘蛛网铲干净,把黏液处理掉。你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打几盘游戏,问候你的初恋情人,幻想自己如何英明神武的把她从巴克山族的魔爪里拯救出来。”
罗汉说完回到房间,用一只手拧下自己的另一只手臂,挂在陈列架上。他又从架子另一端摘下一条神经线复杂的暴露在外面的机器手臂,装在肩轴,这条手臂咔吧一声绽开了五只用途迥异的工具手:锋利无力剪刀、刚劲无比矬铲、美颜无比磨皮、柔韧无比毛刷、和强力无比消毒。这条手臂的肘踝处钢印着阿拉伯文的注册商标,据说其发明者是一名印度美甲师。
巴比蹲在一旁,黑眼睛滴溜溜的盯着那条手臂,他认为,那条手臂归他所有。看到罗汉甩着胳膊往舱外走去,巴比立刻一路小跑跟在罗汉脚步后面。
宇宙安静极了。
白龙熄灭了引擎,不发出一丝动静。
罗汉挥舞剪刀,丝网因此产生的微妙震颤,把聚集在周围的能量弹奏成歌,声音的信息在无声的真空中流向远方。在未来,罗汉将与这些歌声重逢。
将一艘太空飞船打理得像一枚指甲盖儿一样,这任务堪比给宇宙擦桌子,在通常的家政服务条款中都会明文拒绝这种工作。可是罗汉与白龙之间签署的劳动协议随着地球的毁灭一同失效了。实际上在蝉发出指令之前,白龙和罗汉就谁该打扫舱外空间这件事已经争论了数日,信息量之大在人类法庭上足够争锋百年。如果地球还存在的话这场合同伦理战该被写进历史——如果地球存在的话便不会发生这场战争——这场争论的价值高于人类已知的一切思考,历史位置仅次于后来发生的宇宙大总统之争。
但是蝉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判了结果,“罗汉。”他叫道。这一声的后果之严重,直接导致了飞船的扫除工作需要三个月才能粗略完成一次,需要七年才能彻底清除一次,“巧合”的等同于人类细胞的更迭期。
于是接下来,所有人都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三个月后。
藏在远方深处的巴克山族开始收网。那些细细的丝线牵起白龙——被裹成一坨漂浮在空中的小小的棉花糖,缓慢的拖向巴克山飞船张开了触须的口器里。
关于昆虫,以及那些和虫子差不多的小东西,威猛先生这样说过:他们的口器连结着不同的区间入口,他们可以将你一口一口嚼碎,然后一粒一粒的丢过去,再组装成另一件他们喜欢的东西。不过别害怕,这事从来没有发生在人类身上,除非那些虫子足够庞大。
之前消失的那个蹦蹦跳跳的荧光质的金属头壳又回到了蝉的视野里,紧随其后的巨大无比的水熊虫样的船身也再一次缓步走来,远远的朝着白龙张开了大嘴。
速度太快了。
呜的一下,白龙的锅盖尖儿就顶到了大黑虫的上唇。
“罗汉!”蝉叫道。
“我把船体表面打扫干净了。”罗汉回答。
“但我们被困在一个茧里。”白龙补充,“我们会被整个儿吞下,没有胜算。”
在大黑虫口腔里面,区间与区间之间的压力差扭曲了时空,虹吸式的通道漩涡将吞入其中的物质撕碎。
从塔吉锅边沿儿上的一个点开始,粒子呈次方的速度离开了组织,逃出万有引力定律,呼啦啦的滑入大黑虫嗓子眼儿后面的洞里。
蝉从一个指头尖儿开始,感觉到身体松散。他想说话、发问、叫喊,可是声带松散成一片薄薄的沙地,颅腔里只听到尖锐的耳鸣声。转瞬间,随着耳鼓发出嘭的一下,声音全部也消失了。
基因链啪啪断裂,发出一众水泡此起彼伏的破裂的动静,像一群拥挤的沙丁鱼在身体里无声的颤抖。
颤抖停止了。
蝉如梦初醒,睁开——但他很快意识到他的眼睑不见了,与此同时眼球也不见了,实际上他的鼻子、喉咙、关节、韧带、血管、心肺,什么都不见了。
可他却想起了一切:他记得自己的身体从一个受精卵细胞开始,一分为二,在子宫里安全而孤独的长出手脚、感官系统和大脑;他不情愿的被扯到这个世上来,强光刺眼,空气生硬,他哭的撕心裂肺;他听见自己的骨骼酸痛的生长,不合脚的鞋子把脚趾的表皮和皮下组织摩擦分离并注满液体,和同学打架、被猫抓破的伤口底层肉芽组织在三天后开始增生,反引力练习中的失重感令他昏昏欲睡,地球爆炸产生的光芒晃眼得遮蔽了太阳。
三十年,实实在在,此刻被夹在时间虚妄的缝隙里一晃而过。现在这里不再有光,也没有黑暗。他伸出自己的幻肢——那么完整、轻盈、巧夺天工,他毫无理由但清醒确凿的认识到血肉已经消亡,所谓的自己只剩下一个意识,以信息的形式漂浮着。
这就是死亡吗?
这是永生吗?
是谁开了这个残忍的玩笑?
在宇宙的深处,没有声音回答他。
在宇宙的深处,有一张脸,认真去看就没了。
在宇宙的深处,有一首无词无调的尖锐之歌。
宇宙深处令蝉困惑。
他曾代表人类首次到达“无限趋近于宇宙尽头”的那烂陀星,却被告知那里是“宇宙的中心”,那么他现在所感受到的“宇宙的深处”又是哪里?他感受到自己漂浮在一个奇怪的维度里,万事万物都好端端的放在那里,地球完完整整,著名的66号公路上奔跑着一只健美飘逸的阿富汗猎犬。
“没什么事”——远方传来第一个信息,“我先挂了”——这是后半句。
通讯系统中断了,“人类人类还是人类”峰会呲啦一下消失于画。
他困惑自己既已失去了作为“人”的肉体,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说,那么这些感受从何而来?如果他把自己投射到一只狗的身上,他孤立的、个人的、虚构的、非理性的意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活动吗?他和世界之间依然保持着对立的、荒诞的、嫌弃的、失望的关系吗?
唯有死亡。作为唯一的归宿,对于存在产生意义。他将到那里去,携带着敌意,全力捕获一个所谓终极的答案。
他开始下沉,不由自主的贴近地面,一种回到子宫的温暖安全的感觉愈发强烈,他浑身上下都舒服极了。他像岩浆一样流淌,像风沙一样飘摇。他变成了一块锋利的石头,石头开始发光,他抬起头,发现自己照耀着整个宇宙。而他同时感觉到,自己正是宇宙本身。
接着是一阵收缩,宇宙一下子回到了最初。
所有的能量也开始回收,直指自己,向内爆炸。爆炸后的能量并不扩张,而是继续向更深的内部塌缩。时间和空间折叠在了一起,宇宙在一个层级一个层级的消失,他的一切情绪与思考也像卡牌一样被一层一层的抽空。
宇宙深处的有一张脸始终跟随着他,突然靠近他,迅速的从背后穿过了他。
他不由自主的追随而去。在虚无的真空里,他们彼此追逐,无限的接近对方,又猛然跳远。那个人像是宇宙之外的存在,为了填补宇宙空虚的漏洞。他渴望极尽的发光、膨胀,充满了炫耀和占有的欲望,想将对方抓住和被对方吃掉。
那张脸突然掉转方向从正面撞向他。
Isu!
他看清楚了。他叫喊,惊愕万分,那种震颤的体验又回来了,所有的感觉瞬间涌遍全身。他感觉火辣辣的,又冷嗖嗖的,一阵阵的痉挛。
一只冰冷的手从这个维度仅有的方向——四面八方硬生生的将他拽出了这个狭小的时空。
“罗汉!”蝉终于叫出了声音。
他恢复了呼吸。
他用手摸自己的脸——实际上是他的宇航服头盔,触觉和所有的知觉都回来了。他屁股底下坐着“塔吉锅”的锅盖,手边是锅顶帽尖儿的“烟囱”。
罗汉扭动脖子,一些断断续续的干扰信号通过通讯系统传达到蝉的头盔功放。
真空之中万籁俱寂。前方,不知名恒星的光芒松散而遥远。这一切从正面看来和先前没有什么不同。
“别高兴的太早。”罗汉说。
在背面,飞船位于蝉身后的一部分不见了,像是被利器一刀斩落,露出肉眼无法窥探的熔融状流动的像素格。在更远的背面,宇宙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光源、信息、物质、能量。巴比从船舱钻出来,沿着像素格熔岩攀爬上飞船顶棚,与蝉背靠着背蹲坐下来。此时的巴比高大、壮硕、毛茸茸的、黑白相间,一边在蝉身上蹭背一边想象着竹林。
“巴比!”蝉蹿了起来,升得很高,腾空伫立,对着眼下这只仰面躺倒的熊猫惊叫道。
巴比失去背靠,仰面躺下,对着半空中的蝉就地打滚。
罗汉伸出长长的胳膊,把蝉从高高的空中拽下来。蝉一边下降,一边不由自主的在空中打转,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他发现无论自己往哪个方向望去,都只有一半的视线范围,在这一半的视线范围内又同时镜像显现着另一半的景物。这种感受用理论解释起来就是,相对于先前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在这个时空被折叠了。通俗的说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对面就是背对背,背对背就是面对面。因为在绝对的背面是一无所有,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也无法到达。绝对的背面本身是对时空的否定,是不存在。
“欢迎来到扇形区间。”白龙说,并慢慢掀开自己仅剩一半的身体,像一只在深海中张翕吐纳的蛤蜊。
与此同时,巴克山飞船上一片混乱,几百万种虫子瞪着复眼、拍打着鞘翅、摩擦着好几对手脚,他们发言、表决、倡议、交头接耳,嗡嗡作响。
上一次抓捕失败是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个名叫路易斯的恐怖分子一刀剖开宇宙区间的结界,钻出布朗夫人的子宫,以一个新生儿的形象降生在地球上。人类以为这是生理学家爱德华兹和妇科专家斯蒂普特干的好事——他们接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试管婴儿,开创了人工辅助生育的历史。接下来第二例、第三例、第四例试管婴儿相继在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降生。接着就一发不可收拾。爱德华兹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对于星际守卫者巴克山族来说,事情远比“科学的冒险”和“道德的沦丧”要严重得多。事情发生后,三成的高级将领剖腹自杀,五成的责任人离职流放,八成以上的员工陷入没完没了的集体检讨,因此患精神失常者的比例由于日益扩增而变成了多数派,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变得越来越宽容,自由和先锋成了政治家和艺术家追求的主题。但追根溯源,事实的真相却是,如果现在依然遵从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精神鉴定指标来定义的话,巴克山族早就找不出一只正常虫了。
那次事故作为巴克山整个种族的创伤,在历史上、在记忆里、在一代又一代的繁衍中,以遗传基因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以至现在,终于到了伤口再一次被撕裂的时刻,一种隐藏在巴克山族内部的现代性集体无意识的焦虑症大规模爆发,一半以上的虫子在群体性恐慌中晕厥——苏醒——再次晕厥。
很快,饱受神经症折磨的母亲们开始产下数以亿计的假死性虫卵,致使整整一代幼虫完全丧失了自我孵化能力。政府当局当即决议立刻调正船头,一雪前耻,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四名在逃凶犯。
巴克山飞船内,唯一的人类(很可能是全宇宙仅存的人类女性)坐在床边,正在把一只脚伸进黑尼龙丝袜里。接着是另一只脚。她站起来,把大腿和屁股也塞进去。接着是乳房、胳膊、脑袋,最后拉上拉链,一丝不漏。这种古老的合成纤维可缓解人类在突破区间界限时产生的跨维反应,效果非常有限,但仅就保证穿越过致命的变形空间后身体(也可能是尸体)复原时不至于眼斜口歪这一点功能,在人类偏执的追求肉体完整性的伦理体系下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Isu所知,这种超级尼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如果将其编织的纹理有效的按二进制算法解读的话,就能够破译出上帝的藏身之所。在地球毁灭之前,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类曾经汇聚在一起,全力以赴的想要得到这个答案。当然,这一切都让一个蠢货给毁了。
根据宇宙公约第一守则:创造事物的本质就是破坏事物。生命物质的外在关联由一种相互屠杀的模型组建,任何以(包含但不仅限于)食用、繁衍、复仇、雇佣等名义对生命体进行的毁灭性的伤害均属合法;非生命体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对生命体进行任意程度的伤害均属合法;智能生命利用低等生命或非生命物质作为工具对自己及其他生命体进行伤害均属合法。非生命物质的内在归宗于同一源体,外部的一切破坏与改造不被视为对非生命体的伤害。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不可转化。无论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无论直接、间接、主观还是被动的对宇宙源体造成威胁,其物质及灵魂将被丢出宇宙之外——即绝对流放。
毁灭地球的行为无论出自于那烂陀星战舰、蝉、还是宇宙的意外,都完全符合上述守则,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巴克山族接到的是一道来自交管部门的通知:一艘地球飞船未按申请方式使用赛里斯轨道,严重违反了高速行驶安全规范。接下来是来自公安部门的通知,要求以恶性逃逸罪逮捕一艘在星际间流浪的原地球飞船。接下来是区间非法入境罪,定性为情节严重,疑犯凶险可直接击毙。
Isu穿好防护服,轻巧的迈进驾驶舱,开启人工操作模式。所有的虫子“乌”的一下全部贴在舱壁上,用自己最有力的工具抓牢壁板。
缓步的水熊虫停下脚步,开始自我塌陷,像显微镜下细胞分裂过程的一次倒放,巴克山飞船一块一块的缩进去,最终消失在宇宙的一个点上。
然后在宇宙的另一个点上冒出来。它长长的身体发生了一次不完全折叠,看起来像被撅弯了扣在一起的法棍面包。扇形区间之所以成为众多宇宙罪犯的逃亡之地,很大一部分归咎于巴克山飞船如此滑稽的变形——很多罪犯赶往此地仅仅就为了取笑执法者。
蝉在监视器上发现巴克山飞船的时候也发出了开怀的嘲笑声,但在他笑得忘乎所以之际撞上的是全宇宙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他们甚至注册了“海盗”商标,其他海盗需要支付版权使用费才能以海盗的名义打劫)。这是一支很早就失去了家园的游牧种族,在耗尽了自己星球的能源之后,这个贪婪的种族便不得不离开母星,驾驶着东拼西凑的太空飞船在宇宙中流浪。他们需要掠获源源不断的能量用来享乐、维持飞船的运转,以及更为天文数字级的能量来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在宇宙余下的两百四十亿年寿命终结之前从这个宇宙中逃逸出去。
“嗨,新来的!”海盗?船向白龙这样喊话,“打开舱门,朋友,让我们参观参观这可怜的飞船。”
“哦,不。不要。”白龙呻吟着,他的系统遭到入侵,全景天窗被强制开启。
他们的两面四方(扇形区间对四面八方的翻译)围拢着各式各样可随意拆分和聚合的小型飞船,这些飞船的探照灯诡异的扭动着,各种波段的光束彼此交错、旋转、闪烁、晃个不停。
“这不是巴克山族。”蝉手搭凉棚,眯眼观望,听着白龙的哼唧声,“你还好么白龙?”
“我觉得我被扒光了,毫无尊严,只能嘤嘤哭泣。”白龙回答。
“地球人!哈哈,我的朋友地球人!谁能告诉我上一次遇见地球人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海盗?船听起来兴奋极了。
“算起来,也不是特别久的一段时间。”另一个比较深沉的声音也从海盗?船里传出来。
“你喝醉了大副。”那个兴奋的声音说。
“是的船长,我整天都醉醺醺的,我是个该死的酒鬼。”那个深沉的声音非常沮丧。
“威严,给我拿出点威严。”船长语气悄悄的说,但还清晰的传了出来。
“是的船长,我是个邪恶至极的酒鬼,嗷!”
伴随着大副的一声嚎叫,震撼的旋律热烈响起。所有的光束都静止了,它们统一打在一处,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光斑。音乐渐弱直至消失,一个身穿钴蓝色亮闪闪燕尾服的瘦高个儿走出来。他摘下礼帽,露出一对兔耳朵,又摘下兔耳朵(连带着假发),露出一个光头。
最后,他摘下光头,露出一个纯粹的黑脑袋。他那张如黑洞般吸收了一切光与物质、完全无法探测的脸上,绽开一道猩红色月牙形上翘的嘴。
曙光来了我叫你
赞赏
人赞赏